
兒時的年味兒
文/陳孝輝
兒時的年味兒是從臘月就開始的。一進入臘月,人們就開始買年貨,殺年豬、大掃除、貼春聯、掛燈籠……到處一片喜氣洋洋的景象。
小時候,臘月二十七八,家家戶戶就開始準備團年了,一家吃一天,我爸是大哥,先從我家吃起。爸爸在廚房里用砍刀宰著臘豬腳、臘排骨、土雞、土鴨等,媽媽則在煤炭灶臺上炸著滑肉、炸魚,炒著椒麻雞等。我們姐妹倆這時總會著去灶屋(那時我們管廚房叫灶屋)望嘴兒,圍著灶臺,眼睛直溜溜地瞅著鍋里的肉和魚,鼻子吸著撲鼻而來的香味。
“哇,好香喲!”我們兩姐妹在一旁感嘆道,口水在喉嚨處咽了又咽。特別是我那調皮的小弟,在一旁喊著:媽媽,我要吃……媽媽瞧著我們那“好吃樣”,就會拿塊炸魚或椒麻雞給我們吃。那滑肉的香、魚肉的香、椒麻雞的香混著燉臘豬腳的香從煙囪里飄向院子里的上空,整個陳家院子都彌漫著香味——那是年的味道。
“吃完你們就到外面去挑蒜花、劃雞蛋、淘菜、摘折耳根、刨洋芋……”媽媽一邊炸肉一邊笑著說道。
我和妹妹各自往嘴里塞了一大塊椒麻雞,鮮香麻辣,回味無窮;那炸魚可不能往嘴里直接塞,有刺,要慢慢吃。魚肉被淀粉裹著,炸得金黃金黃的,咬開時,嘎吱一聲,外焦里嫩,魚肉鮮香,大快朵頤。
我們舔著手指殘留的椒麻汁兒,余味未盡。大家圍著煤炭地爐,摘著蒜苗、折耳根、芫荽、豌豆尖、白菜,挑著蒜花,剝雞蛋、劃雞蛋,刨洋芋……
“蒜花”是我的家鄉重慶開州特有的一道菜,先把蒜苗洗凈瀝水,再切成小段后泡水,然后用繡花針一針一針地挑蒜斷的兩端,這時的蒜花還不怎么像花,得把挑好的蒜花放進水里泡上,這時你會發現蒜花開始慢慢地綻開,似一朵花兒含苞待放,直至全部綻開,一朵蒜花才算得上是一朵真正的蒜花;劃雞蛋得兩個人配合才能完成,一人拿著剝好的雞蛋,一人用細線往雞蛋劃去,劃兩下,雞蛋成了四瓣,放入瓷盤的邊緣,圍上一圈,中間再放上炸開的蒜花和芫蓿,“蒜花雞蛋加芫蓿拼盤”這道菜在我們重慶開州過年都會出現在餐桌上,沾上特制的味汁兒,那是一個美味。(兒時的雞蛋是非常稀缺的,一般都是留給挖煤的老爸吃)。現在我們每年過年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,必是吃得精光的一道菜。
廚房里爸爸媽媽忙得熱火朝天,案板上的菜品是越來越多——蒜苗辣椒炒臘肉、川味香腸、開州頭碗(滑肉蒸一下澆上味汁再燙一點兒豌豆尖或甜菜在上面)、臘豬腳燉洋芋干加干豇豆、粉條燉雞、梅菜扣肉、水豆豉拌折耳根……看得我們是直流口水;我們姐妹倆幫忙打雜——擺桌椅,拿碗筷,端菜,舀湯,擺酒水。這酒水里有我最喜歡喝的葡萄酒,那時的葡萄酒不似現在的干紅有點兒澀,那時的葡萄酒可能就沒有添加劑,就光是葡萄吧,甜甜的。
菜做得差不多了,爸爸從廚房里走了出來,拿出幾個酒杯往杯里倒了一點酒,叫我去舀了幾小碗米飯放在桌上。“爺爺、奶奶、媽……你們喝酒……”爸爸這是在喊“老輩子”(逝去的親人),“喊老輩子”是在重要的節日里才有的儀式,過了幾分鐘,爸爸把酒倒在了地上,喊“老輩子”們都下了席。
“去,喊你爺爺、三爸一家、幺爸一家都過來吃飯。”爸爸笑著說道。
我屁顛屁顛地跑去喊他們來吃飯,我的腦海里想的全是那兩桌子好吃的美食。
“快,快到屋里坐。”爸爸一邊熱情地招呼著爺爺和叔叔嬸嬸們,一邊把門關上了。我不知道為什么團年要關大門,且是中午?我婆婆說那是很久以前就流傳下來的習俗,具體的她也不知道。
我上網查了查相關資料:在我國江南一帶,每到吃年夜飯的時候,家家戶戶都要關起大門,不能大聲說話,不能敲擊碗筷。吃完年夜飯的碗筷被收拾干凈后,再打開大門——這叫做閉門生財,開門大吉。相傳,這種做法是為了哄騙鐵拐李。
據說到了每年的最后一天,玉皇大帝都要了解民間的生活狀況,于是就派鐵拐李下凡查看民情。鐵拐李為八仙之一,是個跛腳叫化仙,因此便在人間吃年夜飯的時候,提著要飯的籃子跛著腳沿街到各處各家乞討。討完飯后,鐵拐李把討來的東西帶給玉帝老爺子看,誰家窮誰家富,一看就知道了。據此,玉帝老爺子就讓富人一年遭幾次災,不要太富;窮的則讓他發幾次財,不要太窮了。
這事兒慢慢傳到了人世間,一個精明的商人知道了這個情況后,很快就想到了應對辦法。到吃年夜飯的時候,這戶人家把大門關得嚴嚴緊緊,家人誰也不許大聲說話。等鐵拐李來討飯時,打開門,桌上什么也沒有。鐵拐李一看,認為這戶人家窮得連年夜飯都吃不起,于是就大發慈悲,悄悄在這戶人家的門口放上幾個金元寶就走了。就這樣,這家人越來越有錢了。
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。別家也看到了他家發財的原因,便都紛紛跟著學起來。后來,鐵拐李見家家戶戶都關著門吃年夜飯,便知自己下凡探察之事已被人們覺察,就不再到人間來討飯察貧富了。但是,關起大門吃年夜飯的習慣,卻據此流傳了下來并延續至今。
大人一桌,小孩兒一桌,大人們喝著酒擺著龍門陣——述說著一年的悲與喜,一年的收成……小孩兒這一桌,那橙汁和葡萄酒只剩下空瓶,桌上的美食被我們搶著吃,好一個風卷殘云!媽媽在一旁說道,“你們慢點兒吃,廚房還有。”
年三十,是我們小孩兒最期盼的——可以看春晚、玩甩炮兒、放沖天炮兒,最重要的是可以收到壓歲錢,雖然沒有多少,但收到壓歲錢的我們開心極了。
大年初一,小孩會穿上新衣、新褲、新鞋。我們家姊妹多,能穿上一雙白網鞋或是一雙膠鞋都能高興好多天。新衣一般都是給小妹和弟弟買,他們會穿著新衣到院子里轉悠半天。
大年初一,是要吃湯圓的——這一習俗在家鄉不知流傳了多少年。
爸爸和媽媽一早就在廚房里做著湯圓,有紅糖餡的、肉餡的。肉餡湯圓的餡要提前炒臊子——臘肉、煎豆腐、蒜苗、豌豆尖、炒雞蛋一起炒了做成餡,大家都超愛吃肉餡湯圓。做湯圓要講究技巧,做不好會露餡,會厚薄不均。小時候的我沒有做過湯圓,已為人母的我雖然會做湯圓但做得不好,做得厚薄不均,有時甚至會露餡。我的婆婆總會語重心長地對我說:還得好好學,他們都愛吃,得傳承下去。
湯圓在鍋里咕嚕咕嚕,爸爸往鍋里舀上一點冷水,過一會兒湯圓一個個從鍋底飄了上來。“再煮一會兒就好了。”爸爸說道。
“來,給爺爺端去。”媽媽一邊舀湯圓一邊對我說道,“來,再給爺爺添幾個湯圓過去。”
大年初一,除了穿新衣,吃湯圓,我們還得給爺爺拜年。我們姊妹幾個便提著禮物和爸媽一起去給爺爺拜年,爸爸點燃了鞭炮,我們捂著耳朵兒,頓時煙霧繚繞,一股火藥味。給親人拜年也是能收到紅包的,那時的紅包有兩元、五元、十元,收到五元、十元算是收到的大紅包。
拜年要持續好幾天,我們沒有外公外婆,從來沒有見過他們,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離開了人世,這是一種遺憾。小時候的我特別羨慕有外公外婆的孩子——他們可以去給老人家拜年,收到他們的紅包,他們還可以依偎在兩位老人的懷里撒嬌,感受暖暖的溫度和愛……
正月十五是送年了,這一天過完,年就過完了。這一天又叫元宵節,早上是要吃元宵的,晚上則要在地壩的邊緣點上一排蠟燭,家里每個房間的燈都要打開。那時家里的燈泡是鎢絲燈,平常都是舍不得開的。還會點上沖天炮,歡送年的離去。
十五的晚上還有個習俗——摸青。摸青就是在別人的地里去摸些豌豆尖、蒜苗、芫荽、白菜苔、蘿卜……回家里去煮來吃,寓意會帶來好運。如今我們搬進了城里,沒有去摸青了,但有的人會開車去鄉里摸青,把農戶家的菜地搞得一片狼藉。這哪里是摸青,簡直就是偷菜了,辛苦勞作的農戶那叫一個苦惱……
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如今已成為陽光開朗大男孩的母親,那兒時的年味兒似乎離我越來越遠,卻也好像沒有離開——它一直在我的心中,縈繞心頭……
作者簡介:陳孝輝,供職于重慶白術商貿有限責任公司。
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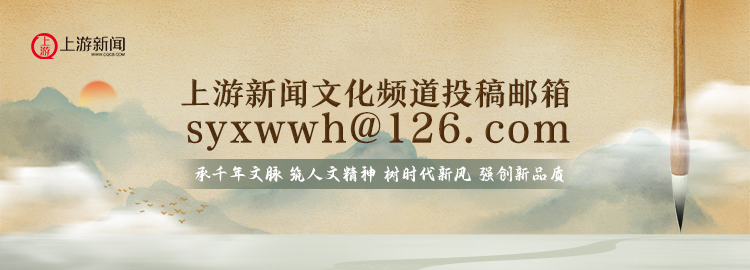
編輯:朱陽夏 責編:陳泰湧 審核:馮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