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磨坊中流轉的時光
文/陳春明
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,能飽飽地吃上一頓白面饅頭和面條,基本上是過年或客人才能享受的待遇。那時候的面粉面條幾乎是純手工的,離我家很近的官廠,就有一個加工面粉面條的磨坊。
磨坊建在寨子古老的炮樓里,背靠寨墻,墻體下半截青石、上半截土木,有規則地分布著一些內大外小的窗子和射擊孔。一樓是生產加工車間,二樓三樓是保管室,除了老掉牙的手搖壓面機外,再也找不到半點機械化的影子。磨坊外有一塊全寨子最大的地壩,除了孩童嬉戲的笑聲外,偶爾還有大人提著麥子兌換面粉面條的身影。
維持運轉的只有二十出頭的父親和一頭老黃牛。父親做事一絲不茍,噴水翻攪、石槽碾壓、吊篩篩搖、風車吹揚,除沙后的麥子在磨盤上堆成了一座小山。老黃牛戴著眼罩沿著固定的軌跡,慢悠悠地數著它邁過的春夏秋冬。轉動的大石磨發出嘰嘰嘎嘎的聲音,像一臺陳舊的唱機,合著老黃牛踏出的節奏唱著古老的歌謠。磨眼中插著一把筷子,攪動著周邊的麥子涌向兩扇石磨之間的縫隙,父親邊向磨盤添加小麥,邊用棕掃帚清掃磨溝里的麥面倒進籮柜的肚子里。籮柜隨著石磨傳遞的聯動,像螺陀一樣不停地轉動搖擺,發出有節奏的哐當聲。面粉如雪花,鉆透籮布的孔縫,紛紛揚揚飄進籮筐里,散發出誘人的清香。
把面粉倒進木面盆后,父親熟練地加入清水、食鹽、食用堿,反復揉搓面團,直累得滿頭大汗。面和好后,又緊著搖動輪盤搖把,轉動面輥裹纏面皮。面機像織布一樣,連綿不斷地吐出“面布”,面輥又把面布裹成“面錠”,依次排在面槽上,等待著被再次碾壓的命運。等到面皮薄如牛皮紙后,在完成了撤換面刀、調試縫隙、咬合面皮等動作后,父親再次搖動了輪盤搖把。面機源源不斷地吐出綿軟的面絲,父親揮動竹面棍把面絲挑成半人高的“面簾”,依次排在面架上。地壩的竹木曬架,是最招搖的存在。整齊擺放的“面簾”如一匹匹白練隨風起舞,掉落在地上竹篾曬席上的面條和著揮灑在空氣中的面香,讓過路的人饞得直吞口水。
夕陽西下,父親舉起又長又寬的板刀,在面板上把干透的面絲截成一把把規規整整的面把子。等到舊報紙或牛皮紙包裹著的面把子碼垛結束,父親對自己的“作品”露出了滿意的微笑,嘴上叼著葉子煙桿、背著雙手,吹響了回家的口哨。
隨著社會形勢的進步發展,磨坊已不能滿足百姓需要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,生產隊把磨坊搬到一個叫石壩的地方,官廠磨坊被拆得連一塊瓦片都沒有剩。石壩磨坊生產模式并沒有什么變化,只是規模擴大到2 個人、2盤大石磨、2 頭老黃牛。
父親在石壩磨坊沒干多久,就當上了生產隊記分員,后又被推上了生產隊長的位置,帶領鄉親們種辣椒、生姜、地瓜、藥材、甘蔗、毛煙、茶樹等經濟作物,在荒山荒地栽植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柑子等果樹,田邊地角栽桑養蠶,興辦雞、鴨、豬、牛養殖場,購置手扶拖拉機、機耕船、脫粒機等農用機具,挖塘修路、改土造田、開荒辟地、改造電網等大事好事干了一件又一件。萬壽6隊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隊,一個勞力一天能掙到5毛多人民幣,比鄰近的5隊整整高了10倍。父親雖然兩次被評為涪陵縣(編者注:現為涪陵區)勞動模范,多次被縣(編者注:現為區)、鄉、村評為農業學大寨先進個人,但磨坊“教頭”的角色卻從來沒有離棄過。
人們倉里有了糧食、手里有了活錢,吃白面饅頭和面條就變得容易多了。父親覺得磨坊是時候有所改進了,思量再三,得出了水能磨面最劃算的結果。說干就干,父親帶著鄉親們在萬壽橋截斷了萬壽河,把舊河道填成良田,利用新河道的落差建起了全鎮第二座水能磨坊(第一座為老街水巷子磨坊)。水車帶動石磨唱起歡快的歌謠,結束了磨坊人推牛拉的古老歷史。
1981年,土地承包到戶,白面饅頭和面條成為了家家戶戶的家常便飯。隨著鎮街電動磨坊的出現,萬壽橋磨坊水車轉動的次數越來越少,最后不得不關門大吉。但去街上碾米磨面的輪子實在難等,路程也遠,來回一趟大半天時間就搭進去了。父親一下子看到了這里面蘊藏的商機,和3人搭伙,利用生產隊閑置房屋,購買了打米機、粉碎機、磨面機,建起了紅紅火火的新磨坊,輻射周邊四五個大隊,20多戶農戶依托磨坊干起了專業加工面條的營生。
聽著電動機高速旋轉的哨音和機器撞擊出的磨坊新生的歡叫,忙碌的汗水和收獲的喜悅一下子溢滿了父親的臉龐。
作者簡介:陳春明,重慶涪陵人,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、涪陵區作家協會副秘書長,有散文、詩歌、小說、評論等發表于各級報刊和網絡媒體。
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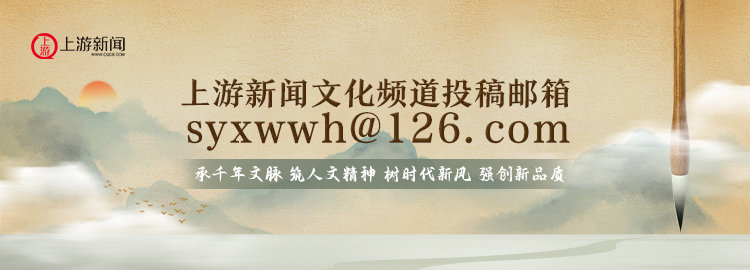
編輯:朱陽夏 責編:陳泰湧 審核:馮飛
上一篇:縉云丨夏遠蓉:候鳥
下一篇:縉云丨楊樹弘:涪江河行吟(9首)